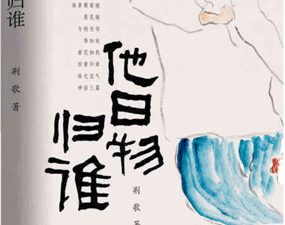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德国理论家瓦尔特·本雅明对艺术作品的价值来源进行了追溯。本雅明认为,古代社会强调的是艺术的崇拜价值,艺术作品的价值建基于仪式,服务于巫术和庆典;从文艺复兴开始,对于美的市俗追捧渐渐取代了艺术的仪式功能,艺术作品的本真性取代了其崇拜价值;现代社会强调的则是艺术作品的展览性,其功能体现在供人观看和欣赏,艺术作品的展览价值开始凌驾于其本真性之上。本雅明将1900年左右作为一个分界点:随着摄影和电影技术的成熟,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机械复制的时代。当一张底片可以洗印出无数张摄影作品,当一盘电影胶片可以大量拷贝,真品和赝品之间的界限开始日渐模糊。
按照本雅明的理解,只有艺术作品的原作才具有本真性,这种本真性是无法复制的。艺术作品的独特价值就根植于这种本真性之中。艺术作品的原作具有独一无二性,而复制品则不具有这种独一无二性,因此也不可能具有艺术作品的本真性。特别是在机械复制时代,当独一无二的艺术作品被拍成照片,人们用欣赏艺术作品的图像代替欣赏艺术作品本身的时候,缺少了艺术作品空间上的在场,就使得艺术作品的图像彻底成为一种被削减了的艺术。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是什么被削减了呢?本雅明给出的答案是:灵晕(aura)。本雅明将灵晕理解为某种遥远之物在近前的独一无二的显现。在远与近之间存在一种张力,灵晕在此得以涌出。本雅明悲观地认为,在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的灵晕将无可挽回地消逝。

我们可以看到,本雅明对“灵晕”概念进行了一种空间化的表述。在他看来,灵晕来自空间距离的某种错置。遥远之物显现于近前,使我们得以感知。一旦这种距离彻底消失,灵晕本身也将随之消逝。换言之,某种必要的距离是灵晕存在的前提。在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灵晕的消失恰恰来自这种必要距离的消失。当这种距离被跨越以后,主体与艺术作品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无可挽回的变化。对于本雅明来说,艺术作品的灵晕不是其内在和固有的,而是与其所处的位置密切相关。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一个论断:客体所在的位置常常比客体的内在属性更具优先性和决定性。斯洛文尼亚理论家齐泽克将法国艺术家马塞尔·杜尚的《泉》看作这一论断的完美诠释。小便池本身毫无艺术性可言,它的平凡和日常很难让人将其与艺术联系起来。但在某种特殊的情境下,当它占据了美术馆中的一个位置,进而占据了艺术史中一个特定位置的时候,它就被提升到了弗洛伊德所说的原质(the Thing)层面,成为一件无可争议的标志性的艺术作品。
在这里,艺术包含了两个不同的层面:想象的层面和象征的层面。在想象的层面上,艺术作品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直观形象。在这一层面上,艺术作品具有确定无疑的可复制性,且这种可复制性会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发展,摄影技术的出现使这种复制变得更加精确与高效。但在象征的层面上,艺术作品则要在艺术体制中占据某个特定的位置。艺术体制为我们建构了一个特定的框架,我们总是透过这个框架去理解艺术作品的意义,甚至透过这个框架去界定艺术和非艺术。在这一层面上,不是艺术作品的内在属性,而是其在艺术体制中所占据的位置决定了其最终价值。艺术作品的内在属性与其在艺术体制中所占据的位置未必是统一的。不是前者决定后者,不是艺术作品的内在属性决定了其在艺术体制中的地位,而是恰恰相反,艺术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常常由其在艺术体制中所占据的位置所决定。
艺术体制的变动常常导致艺术作品评价上的巨大起伏。一件艺术作品既可能从寂寂无名变得受人顶礼膜拜,也可能从艺术的神坛上跌落,甚至被排除到艺术范畴之外。艺术体制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它掩盖了不同作品的非一致性,使它们获得共同的作为“艺术”的名称。艺术体制所建构的框架成为我们体验艺术的一种方式,使我们将艺术作品体验为某种具有特定意义和分享某种共同特征的事物。只有当某件作品进入了由艺术体制所代表的幻象构架,它才能被识别为艺术。艺术体制的变动不应仅仅被理解为艺术方法和艺术技巧的演变。在本质上,艺术体制的变动体现的是艺术概念的重新界定,体现的是人们对于“何谓艺术”这一古老问题的重新阐释。
在这一意义上,艺术作品的灵晕并非艺术作品的某种内在属性,亦非艺术作品自身所固有的某种特质。一件艺术作品之所以被人们所承认,是由于其占据了艺术场域中的某个位置,填补了艺术场域中的某个空白。如果我们借用拉康的概念来表述,那就是:一个普通客体一旦占据了某个特殊的空位,就会变成人们眼中的崇高客体。艺术作品的灵晕就是其作为崇高客体所具有的光环,在这样的客体身上,总是有某种东西超出其自身的内在属性,而灵晕的消失则意味着艺术作品身上崇高性的消失。适当的距离是保持这种崇高性的前提,一旦这一距离被跨越,艺术作品身上的崇高性就会烟消云散,重新回到普通客体的位置之上。换言之,不可接近性恰恰是艺术作品的一个本质特征。这也恰好印证了本雅明的论断,即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灵晕消失的必然性。机械复制打破的正是人们与崇高客体之间的必要距离,这种距离的消失直接导致了灵晕的褪去。但本雅明忽略了一点:由艺术体制所建构的幻象空间事实上也在不断调整。正是由于这种调整,使得我们今天谈论艺术依然可能。只要这种幻象空间依然存在,艺术就不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如齐泽克所言,客体的崇高性来自其在幻象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我们无法谈论纯粹现实,因为现实总是被幻象所渗透,被欲望所扭曲。同样,我们也无法谈论纯粹艺术。艺术作品的灵晕来自某种被扭曲的凝视,正是这种扭曲使其具有了崇高的性质。正如拉康对于国王的分析:国王之所以是国王,来自臣民的服从和膜拜。同样,我们可以说,正是艺术作品的膜拜价值使其得以成为艺术。对于艺术作品来说,只有在艺术体制所建构的幻象空间中,才有所谓的灵晕。灵晕是艺术作品中超出自身形象的某种东西,它有待被阐释,但每次阐释又会留下某种剩余,留下某种无法符号化的部分,只有在回溯中才能被辨识出来。在这一意义上,作为崇高客体的艺术还包含了某种超出象征秩序的维度。关于象征秩序之外的维度,拉康称之为实在界。机械复制最多只是在想象界的层面对艺术作品进行了模仿,在象征界和实在界的层面上,艺术作品则是不可复制的。而艺术的独特魅力、艺术作品的灵晕,恰恰来自象征界与实在界之间。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传媒学院)
艺术
后现代
艺术理念
发现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违法、不良信息举报和纠错,及文章配图版权问题均请联系本网,我们将核实后即时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