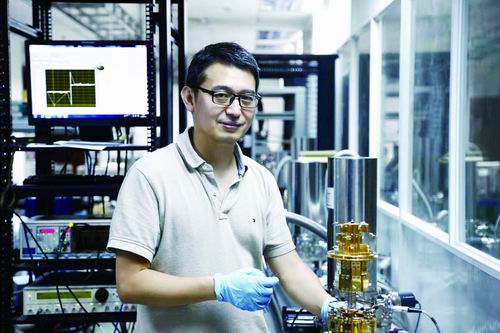
尤立星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胡珉琦
近日,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三号”再度刷新了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处理高斯玻色取样的速度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一亿亿倍!
“九章”背后有一位默默无闻的功臣。他虽然不被大众所熟知,但其名字一直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潘建伟院士团队深度绑定。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微系统所)研究员尤立星,一个被潘建伟称为国内超导单光子探测器(SSPD)“顶梁柱”的人。
不久前,尤立星入选美国斯坦福大学与Elsevier联合发布的第六版《年度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今年7月,他还因在“超导电子学和量子信息处理”领域的突出贡献,获得欧洲应用超导学会(ESAS)颁发的应用超导杰出贡献奖。该奖项全球每两年评选1次,每次仅评选1位科学家。
在国内,将高端科研仪器做到国际顶尖的科学家是“稀缺品”。过去15年,尤立星一直致力于国产超导电子器件与应用成果的研发和转化。他说,他所追逐的并非超导“极限”竞赛。
背后的人
2019年10月,谷歌在《自然》发表论文,称其量子计算机已经实现了“量子霸权”。尽管其一度引发争议,但在当时着实刺激了量子圈。
几天后,尤立星就接到了老搭档、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团队成员陆朝阳教授的“任务”——希望他在5个月内提供100个高性能SSPD,加速“九章”光量子计算原型机的研发。
尤立星团队从事的是用超导技术来做单光子探测器,服务于整个光量子信息领域,无论是量子通信还是光量子计算领域,都与潘建伟团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
“九章”是以光作为媒介实现计算的,而光的量子极限就是单个光子。单光子探测器就是量子极限灵敏度的光测量设备,可以探测单个光子。要是没有这个探测器,用光传递量子信息就不可能实现。
“……需求紧急,请以最高优先级保障,拜托!”潘建伟的微信紧随其后,足见该探测器有多重要。
但只有尤立星自己清楚,这样的需求和极限任务无异。
对于光量子探测芯片,在实验室完成样品到实现批量供应,还要保证较高的平均探测效率,难度升级是指数级的。
“科学家的研究思维和产业界的产品思维截然不同。”尤立星说,前者想的是怎么在实验室把一个芯片从0到1做出来,同时,竞争对手追求的是如何进一步提升单个样品的探测效率;而后者考虑的是如何从1到100实现工程化,不仅要实现较高的成品率,还要对用户友好,能解决客户的实际问题。
尤立星的与众不同是他从0开始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想到了1到100的过程。
作为光量子信息领域的一个关键器件,其国外封锁从始至终。早在2013年,国外实验室SSPD的最高系统探测效率已经达到90%,但进口到中国的产品远不及这一水平。
国内单光子探测器研发起步稍晚,同时期,尤立星团队能达到的最高探测效率只有70%多,且一度停滞不前。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困境,其实是尤立星“自找”的。
超导研究存在一个工作温度的问题,选择不同的材料做探测器,将会对应不同的工作温度。“当时有一种热门材料叫硅化钨,它比较容易实现很高的探测效率,但条件是工作温度极低,这意味着需要用昂贵的制冷机来维持环境温度。”
尤立星则反其道而行之,他坚持了一条较高工作温度材料的研究路径,大大降低了应用成本,也让用户使用更加友好。这种材料叫氮化铌(NbN),但NbN要达到与硅化钨同样的探测效率,对材料本身和纳米线加工工艺的精细化要求更加苛刻。
于是,当其他研究团队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在更低的工作温度下获得更高的探测效率时,尤立星却坚持用尽可能低的成本,默默打磨工艺技术。
直到2017年,尤立星团队首次利用NbN材料研制SSPD创造了系统探测效率达92%的世界纪录,竞争局面开始逆转。在达到同等系统探测效率的情况下,SSPD成本更低、更好用,应用空间也更大。
也是从那时起,尤立星开始了SSPD的产业化运作,创立了赋同量子科技。除了探测效率,他还关心产品的成品率,以及不同应用领域技术支持和迭代的问题。
“许多学术研究的套路,就是通过不断刷新指标来积累论文,或者换一种材料发一篇论文。”尤立星坦言,单纯从科研角度出发,选什么材料不重要,追求极致最重要。“但制作科研仪器这还不够,它的最终目的是有用且好用。”
因此,当潘建伟给出了那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尤立星团队才能凭借相对稳定的成品率,用最短时间测试并筛选出符合需求的批量化探测器。其间,他的团队还实现了NbN材料SSPD在光通信波段98%的系统探测效率,并将这一世界纪录保持至今。
尤立星告诉《中国科学报》,他在最“顶尖”的论文中都不是担当第一作者或是通讯作者,他在其中更像是一名支撑者的角色,帮助中国量子领域的诸多科研团队解决实验科学问题,这才是他的价值所在。
管理高手
高端科研仪器的研发通常需要多学科交叉融合才能完成,尤立星特殊的学术背景起到了关键作用。
2003年,从南京大学博士毕业的尤立星开始了海外的博士后研究生涯。4年里,他从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辗转荷兰特文特大学,再到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在哪儿都不安分。他笑言,自己的博士后时光是在“游学”中度过的。
尤立星本有机会继续留在美国,“但跟着国外老板干,总有一种打工人的感觉”。2007年,他选择“回家”。
当时,上海微系统所正计划启动超导单光子探测方向的研究,这和尤立星的研究领域比较契合。于是,他白手起家,建团队、搭平台。
“虽然那些年我一直围绕超导电子学做研究,但并未涉足SSPD的具体研究。在瑞典,我更关注基础研究,内容与高温超导约瑟夫逊结器件有关;到了荷兰,接触的是磁探测相关研究;到了美国,又转向太赫兹探测有关研究。”
然而,正是这段不够“专注”的科研经历让他有了丰富的知识储备,也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很适合做交叉学科研究。他能迅速把握单光子探测器从无到有的技术链条到底需要什么。
SSPD系统包含了芯片、制冷、光学和电子学系统四大部分。“没有人能在所有方向都做到顶尖,我只需在各个环节找到擅长的研究人员或利用已有的成熟技术,最终合力把与仪器有关的科学问题解决好。这才是仪器研发的根本思路”。
尤立星在组建团队时非常注重成员的不同背景方向,有做器件物理的、有做光学的、有做低温的……“我们团队的最大特点就是交叉程度非常高。”尤立星提到,这样的团队组合到了产业化阶段,在解决用户不同环节的问题需求时能发挥奇效。
在赋同量子科技高管张成俊博士心里,导师尤立星最突出的个人能力也许不是科研能力,而是管理能力。
“要让一台实验室仪器变成一个市场化产品,光靠一个人战斗必输无疑。”张成俊说,“尤老师有一种魔力,从不给我们下绩效指标,但总能成功激起我们的内生动力。”
尤立星则笑着回应,自己非常擅长压力传导,他曾把潘建伟的微信一字不落传达给每一位团队成员。这不仅是压力共担,也是使命和荣誉共担。
张成俊还提到,在尤立星的引导下,企业团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从研发到生产各个环节的员工都要走进产品的应用场景中,到高校、科研院所、高技术企业的实验平台,与那些一流学者、专业技术人员交流、向他们学习,发现自己的不足。
公司还会定期把客户使用产品后取得的科研成果介绍给员工,把他们的个人劳动和重要的科研产出以及取得的社会效益联结起来。
“在高端科研仪器这个严重‘卡脖子’领域,没有使命感,我们‘活’不到现在。”张成俊认为,这些正反馈对团队而言十分重要,它会增强每一位员工的精神力量。
2016年至今,尤立星团队每年都获得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资助的上海微系统所“新微之光”奖。“这是对整个SSPD研发团队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们这种团队协作、交叉合作科研模式的认可。”
“消失”的销售
无论何时,高端科研仪器赛道的应用面都比较窄,且赋同量子科技的产品售价也与进口产品持平。但让尤立星自豪的是,他们与国际上其他5家企业在中国市场竞争中遥遥领先,国内市场占有率近80%。
尤立星说,企业目前的商业模式比较特别,由于量子技术的发展非常迅速,用户需求也在不停更新,因此,赋同量子科技提供的既不是完全成熟的固定型号产品,也不是完全定制化的产品,其中定制部分占50%。而这种模式最考验产品团队的服务能力。
“科研仪器研发的最大阻碍就是走不出实验室,与客户需求脱节。”尤立星直言,实验室产品的研制、测量是在精细、可控的环境下完成的,一旦进入应用场景,就会出现许多复杂的影响因素,工作环境变了,产品的适配度就会下降。
而尤立星的产品策略是,始终把和应用端科研人员的配合放在第一位。“我们会把实验室阶段还不太成熟的仪器拿到用户实验室做测试,及时发现问题并作出调整。”
“我们的团队里没有销售的概念,每位员工的定位都是科学家的合作伙伴。我们用专业的语言和专业的用户对话,回应他们的每一项专业需求,从而赢得他们的信任。”正是这种务实的理念,颠覆了很多用户对于国产科研仪器“便宜不好用”的看法。
2022年3月,赋同量子科技走出国门,成功拿下首个欧洲订单;同年7月,其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欧洲Demo中心”正式启用,主要是为承接欧洲用户的试用、科研合作服务;同年8月,尤立星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单光子探测器国际标准经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批准正式发布,这也是我国牵头制定的首个超导电子学领域国际标准。
高端科研仪器一直是重要的国际竞争领域,在量子技术这个中国科学家有望取得优势的“科技制高点”,尤立星呼吁科学界支持并优先使用国产高端科研仪器。
量子计算原型机
高斯玻色取样
发现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违法、不良信息举报和纠错,及文章配图版权问题均请联系本网,我们将核实后即时删除。




